紫阳富硒茶本心(紫阳茶富硒茶)
众所周知,饮茶为中国先民的伟大发现,茶文化堪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根据统计,目前全球饮茶国多达160多个,饮茶人口约30亿。饮茶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目前学界对佛教从中产生的影响多有论述,但对基督宗教与茶的世界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还缺乏深入关注,目前仅就其中的个案问题给以了分析,笔者不惴浅陋拟就此展开系统探讨,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传教士与饮茶资讯的西传
因为茶的使用历史极为悠久,其准确开端目前难以准确判定,长期以来,茶文化专家大致上认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会时期。唐代的陆羽在著名茶书《茶经》中即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该说法被广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茶树根亦提供了有力证据。自先民利用茶叶始,茶文化即逐渐萌芽并不断发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扩散与传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断传入临近的周边国家与地区。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极为遥远,这不能不对茶文化的传播造成阻碍。因为资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时获得饮茶资讯并开始饮茶,目前难以判定,尽管《新约•启示录》第22章包含约翰描述神奇树叶的语句,“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条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练,从神与羔羊的宝座淌出,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上面结十二样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个别论者颇有想象力地认为该“生命树的树叶”即茶叶,但孤证不立,而且该材料并未明确指出为茶叶。目前有准确材料能够证明的是,西方人获得饮茶信息大致为十六世纪中叶,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腊玛西交游广阔,从来访的西亚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饮茶资讯,但仅限于传闻并未亲见,西方人最早亲身见闻饮茶者可能为来到东方进行贸易的商人以及传教士,而传教士留下了较多的文字资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证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伽兹博尔•达•克陆兹到达东方,进入中国一度在广州居住数月时间,最后于1560年返回。克陆兹的见闻被辑录成书,名为《中国志》,公开出版发行,影响甚大,还被欧洲其它国家翻译成多种语言。克陆兹在书中非常清晰地记述了中国人待客之道:
“如有宾客造访,体面人家习常做法为敬现一种称之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质杯中,置于精致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热水带有红色,药味很重,他们时常饮用,这是用略带苦涩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来招待尊贵的宾客,不管是否熟识均是如此,他们也数次请我饮用。”

因为是亲身的见闻与体验,克陆兹的记述虽然文字颇为简略但内容却具体而丰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颜色和味道、饮茶所用的茶具,明确说明了时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这次有关饮茶的具体信息为西方所缺乏。此后,饮茶资讯借传教士这一渠道继续传入西欧:1565年,意大利籍传教士路易斯•艾美达在日本传教,他写信回国时提及,“日本人喜爱一种可口的‘药草’,他们称之为茶”,并且认为,“假使一个人习惯了的话,它是一种味道颇为可口的饮料”。在赴日传教之前,艾美达曾经是一名医师,他在日本传教适逢茶道最终形成的关键期,千利休正潜心钻研,社会茶风兴盛,相信艾美达耳濡目染,对当时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没有更多材料保留下来。
继艾美达之后,西班牙另一位传教士胡安·门多萨再次介绍了饮茶。门多萨信仰虔诚,19岁即加入了奥古斯丁修会,他曾经接受了出使中国、进行传教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最终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未能成行,他应教皇乔治十三之命,广泛搜集前人(很多为传教士)留下的访华报告、信札、著述等多种重要资料,最终编撰成为名著《中华大帝国史》,该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书中对饮茶给以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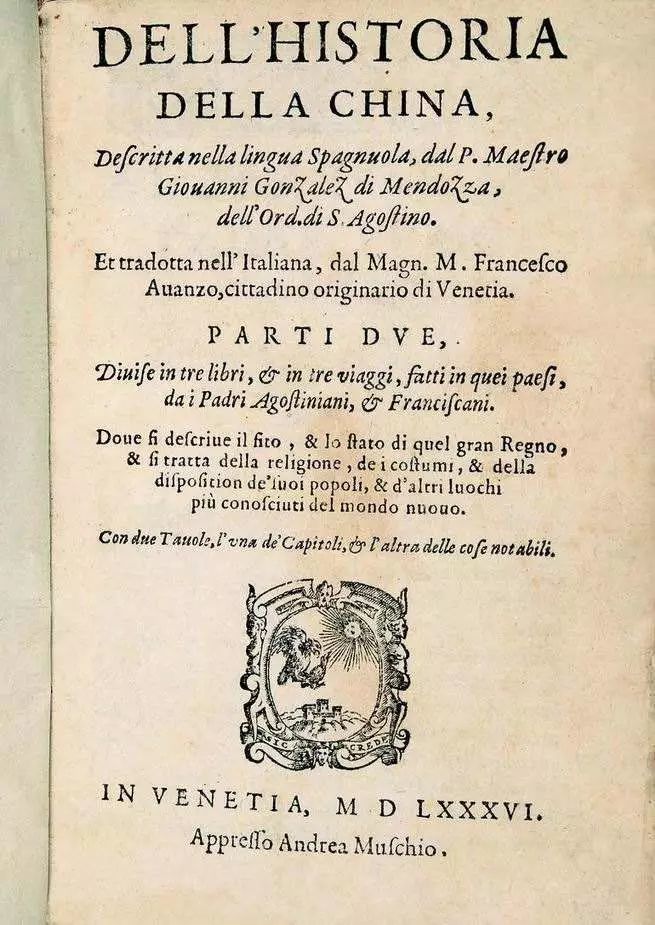
“中国人盛情款待宾客,旋即摆上饮品(bever)、茶食、蜜饯、果品以及美酒,此外,还有一种在全国各地均被饮用,用草药制作而成的饮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饮时须加热。”
《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后引起巨大轰动,可谓洛阳纸贵,仅至十六世纪末的十多年间已经翻译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文字,发行版次达到惊人的四十六版,客观说来,书中关于饮茶的介绍并不新鲜,材料主要源于克陆兹的著述,但该书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国志》所不及,对传播饮茶资讯亦有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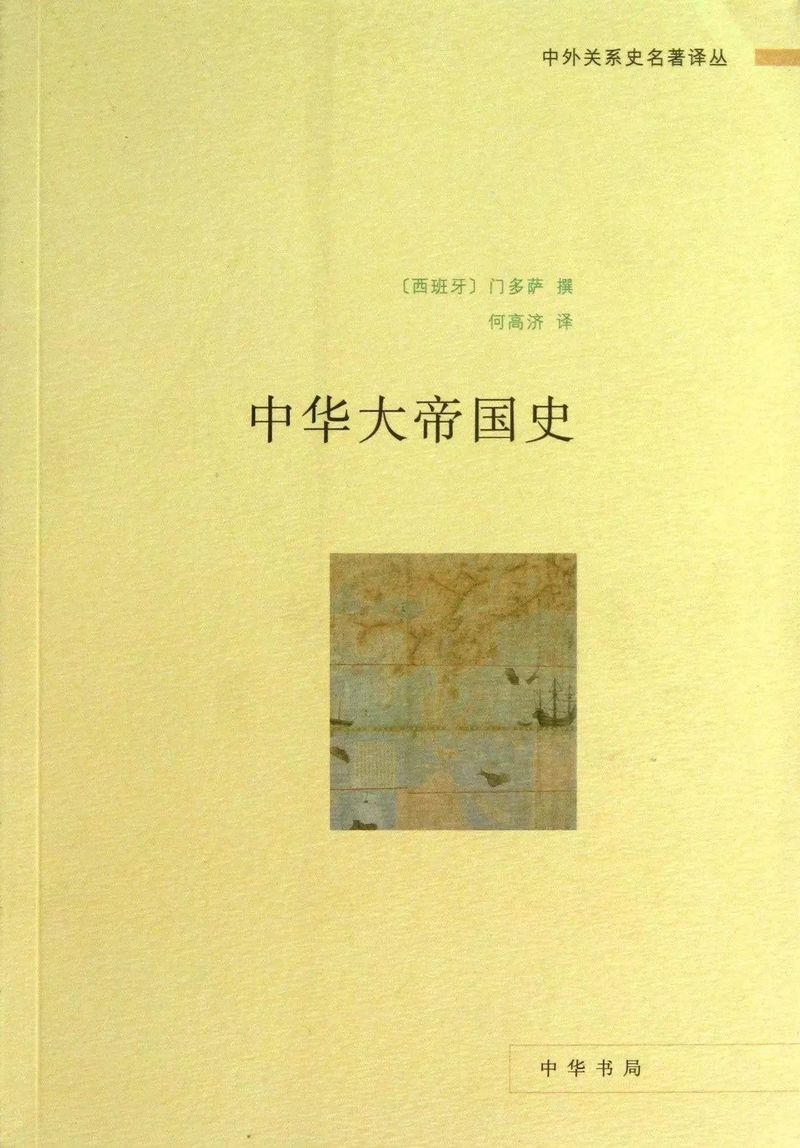
根据现有记述,最早对茶进行详尽介绍的传教士为利玛窦。受耶稣会的差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到澳门,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在华传教历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对茶文化的了解也远胜过其先驱:
“由灌木叶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饮料。中国人饮茶为期不会太久,因为古籍中并无书写该著名饮料的古字,而其书写符号(指汉字)极为古老。的确如此,同样的植物抑或能在我们的土地上被发现。在中国,人们在春季到来时采集这种叶子,置于阴凉处阴干,继而用阴干的叶片调制饮料,可供用餐时饮用或者宾朋造访时待客。待客之时,只要宾主在谈话,主人会不断献茶。该著名饮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饮,需趁热喝掉,其味道难称可口,略呈苦涩,但即便时常饮用也被视为有助于健康。

这种叶片可分为不同等级,按其质量差异,可售价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叶子一磅可售十个乃至十二个金锭。日本调制饮料的方法异于中国:日本人将干叶磨为粉末,取两三汤匙投于滚开的热水壶中,品饮冲出的饮料。中国人把干叶放于滚开的壶水中,待精华泡出后滤出叶片,只饮剩下的水。”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堪称全面而深刻,该段文字对明人饮茶的叙述颇为详尽,美中不足的是,利玛窦认为中国饮茶史不会太久,理由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茶”字,这可能缘于不了解“茶”的有一历史演变过程,茶字则始于唐代。尽管如此,利玛窦仍远胜于其前辈,他不仅详述了明代的饮茶风俗,而且还比较了中日茶法的差异,对制茶与茶的商品价值给以了介绍。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未曾抵达日本传教,他却比较中日茶法的差异,对日本的饮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许得益于其他耶稣会士的记述,多少说明此时有关日本的饮茶资讯已传入欧洲。1615年,利玛窦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奥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法文版三种,拉丁文版四种,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种,英文摘译版一种,该著作的广为传播促进了西欧对茶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利玛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对茶文化给以关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辗转抵达南京,由此开始传教历程,尽管他中间曾返回欧洲,最终还是于1658年卒于广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国志》,其中对茶文化给以记述:
“主人给宾客安排的座位适合其身份地位,……(宾主)落座之后,即刻端来茶这种饮品,按先后次序逐个递送。在某些省份,频频上茶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则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则为暗示客人须告辞了。”
曾德昭对中国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饮茶方法、味道等内容,而是更进一步,掌握了饮茶的礼仪内涵,客人需按照社会规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场广为流行的习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经初现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译版问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两种法文译本问世,1655年出现了英文本。可以想见,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广为流传,其中对饮茶的记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国茶文化。

传教士与中西茶叶贸易
传教士不仅在饮茶资讯西传过程中担当了中介,使与东方距离遥远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这一中国饮品,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了中西茶贸易之中,为茶叶这一实物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中西茶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新航路开辟之后,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东西方交通大开,传教士与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来,成为沟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与商界密切联系:对传教士而言,传教需远赴重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花费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对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传教士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较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汉语,这对发展商业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一大背景下,传教士与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联系,能够在茶叶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时历经波折,先从伦敦出发横跨大洋到达美国纽约,在那里努力寻求帮助,得以乘坐美国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终“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号’远航前往中国,于1807年9月抵达”。在中国拓展传教事业绝非易事,马礼逊虽竭尽全力但仍然难有进展,自1809年起,他因为经济拮据不堪而难以为继,不得不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
“在马礼逊先生与玛丽小姐结婚的美好日子,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礼上宣布了任命书,马礼逊的年薪为500镑。这可视为较为充足的证据:马礼逊此时已经较好地掌握了中文。与此同时,由于他具备谨慎坚韧的良好品性,东印度公司才将其安排在这一独特而辛劳的职位之上。”
此后,作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的马礼逊不再专职传教,而是长期担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其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为茶贸易的迅猛增长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言堪称发展茶叶贸易的关键期,根据统计,正是1760至1833年间,茶叶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渐在公司所购货物中占据绝对优势,甚至在1825至1833年间,茶叶贸易的价值占公司所有商品价值的比例高达94%。可以想象,马礼逊拥有的关于中国的丰富知识,其“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对促进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达福州,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养,1866年即返回香港传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定居,最终病逝于1880年。作为传教士,卢公明的在华传教事业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举步维艰,其本人的生活极为窘迫,经常处于身无分文的悲惨境地,“没有钱来帮助友人,无力做些善事,无法购置一些书籍、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我不想再在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总是因为工资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无奈”。更加不幸的是,卢公明与家人屡遭疾病打击,其两任妻子与年幼的女儿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饱受疾病折磨,喉咙疼痛得甚至一度失声,他的传教事业实在难以为继。经过反复考量,卢公明于1868年投身琼记洋行,参与到了当时迅猛发展的中西茶贸易。卢公明并没有记述自己如何投身茶叶贸易,但在其语言学书籍《英华萃林韵府》的附录中,他详细记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举的茶行中的分工多达数十种,显示出作者对茶叶贸易的熟稔,或许弃教从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对自己在商行的具体工作讳莫如深,但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卢公明熟于茶叶贸易,堪称行家里手。卢公明在琼记洋行工作期间,这一时期该行茶贸易迅速发展,卢公明从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传教士不仅直接投身茶叶贸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时亦与中西茶叶贸易有所关联。比如马礼逊,他除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经担当其他任务,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来华访问时,马礼逊作为翻译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该使团访华的根本目的为扩大贸易,对茶叶贸易颇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务委员会致函阿美士德勋爵时,明确提出以茶叶贸易为例说服乾隆皇帝:“现在,每年东印度公司前往广州的船只……在该地运走大约三千万磅重的茶叶。该贸易对中国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见,能够很好地维持该贸易时,中国政府不会鲁莽丢弃。……他们能够想到,把我们所购茶叶的大部分由其它国家运走,以此削弱我们的地位,可以向他们说明,……英国消费茶叶超过了欧洲其它所有国家,美国的茶叶消费量更小,最终只能是中国受到损失。”
再如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士立,他于1831年来到澳门,不仅曾经投身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有所贡献,而且还多次潜入中国沿海,进行航道勘测等非法秘密活动。郭士立曾随同“阿美士德号”觊觎中国,还成功地抵达了茶贸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到:

“……我们昨日才触摸到陆地,今日已经抵达福州港,黑暗笼罩着大地,难以辨清福州港所处的地形,领港很出色,把我们安全地引导了进来。现在,我们即将到达为欧洲人提供茶叶的重要产地了。茶山四处蔓延开来,这里稻米产量不足,无法满足本地消费,但是其出口的木头、茶叶与竹子数量可观,足以抵消进口稻米与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
临近西方人梦寐以求的茶产区,郭士立急于进行详细刺探,但是当地官员对此已经有所戒备,他虽然已经极为接近武夷山区,但却无法潜入,后来被迫返航。郭士立对潜入茶产区念念不忘,伺机再次付诸行动,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国鸦片贩子戈登伺机潜入武夷茶区,这次两人获得成功,经过考察,他们不仅基本掌握了有关茶树栽培、病虫灾害的知识,还了解了制茶方法、茶叶销售等内容,戈登还很有心机地采集了武夷山优质茶树标本,带走了一定数量的茶种。第二年,并不满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试图再次秘密潜入,进行进一步了解,但颇为警觉的清军进行了拦截,使其无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区的探险活动,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区以及茶学的基本知识,对后来福州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响,而福州后来辟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贸易,便利了中西茶贸易的进行。

之所以传教士能够在商行任职,主要缘于他们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当时人才颇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这种极有价值的服务,对传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职位可以满足生活所需,曲线实现传教目的,由于茶叶贸易为商业公司的主要业务,传教士所提供的服务对茶叶贸易的发展颇有助益,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刺探中国情报,搜集茶学知识,在中外交往中担任翻译,这均直接或间接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宗教领袖与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随着传教士不断将饮茶资讯传回西方,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饮茶在西欧逐渐流行,在英国尤其如此。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闯入东南亚,开展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通过直接购买并运回大量的胡椒与丁香等香料,葡人变得如此富有,以致与远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国相比,葡萄牙的财富亦毫不逊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关注香料贸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潜在价值。荷兰人随后来到东方进行商业探险,“荷兰人运来干鼠尾草,以之交换中国的茶叶,中国人用一磅或四磅茶叶换购一磅鼠尾草,他们将其称为‘奇妙的欧洲草’,……,由于欧洲人无法大量销售鼠尾草——就像他们购买茶叶那样,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价格购茶”。荷兰不意间开启了中西茶贸易,促进了饮茶在欧洲的扩散,饮茶之风在英国影响甚大,后来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国茶文化。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玛丽二世与威廉三世共同担任国王,玛丽二世作为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她在1667年与荷兰的威廉成婚,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两人共同继承了英国王位:玛丽二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执政。玛丽二世钟爱饮茶,她还极为风雅,经常在宫廷之中举办中国式茶会:举办活动之时,玛丽二世特意命令将宫殿布置为中国风格,布置上中国风情的屏风,使用中国进口的茶具甚至名贵的银器,还摆上颇为先进的移动式茶几,步入房间,众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国氛围之中,玛丽二世与一些贵族妇女共同享受饮茶的乐趣。

宫廷牧师J.O.奥文顿对茶也怀有极大兴趣,他还于1699年撰写了小册子《论茶性与茶品》,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对茶给以全面介绍,全书共计五个部分:茶树生长区的土壤类型与气候概况;茶叶的不同种类;选择茶叶的基本原则;保存茶叶的基本方法;茶叶的重要特性。今天读来,可能觉得书中关于饮茶功用的叙述略带夸张,奥文顿认为饮茶几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症,包括尿砂和眩晕,并且能减肥消脂,消解导致胃部不适的酸水,可以帮助消化、预防痛风、增强食欲,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饮茶还能提神益思。J.O.奥文顿尽其所能,较为全面地向英国人介绍了饮茶知识,大力鼓吹饮茶的多种益处,对推动饮茶风气在英国社会的传播颇有助益。
J.O.奥文顿对饮茶极尽赞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对饮茶大加贬斥,典型代表即约翰·韦斯利。约翰·韦斯利为英国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纪领导了宗教复兴运动,影响极为深远,对于饮茶,约翰·韦斯利颇为反感,认为饮茶危害甚大——不仅对个人身体有害,而且危害社会。韦斯利在1748年给友人的信件中详细叙述了自身遭遇:“我无法想象,究竟何种原因导致双手持续颤抖,直到意识到:病症总会在茶早餐后加剧,而停止饮茶大概两三天此现象会消失。调查显示:饮茶对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会产生同样的不良影响,由此可知,这是饮茶导致的结果之一。”约翰·韦斯利进一步论及,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伦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现出类似的病症,并且认定这也是饮茶造成恶果,对于某些人士而言,饮茶的确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类功效饮用英伦本土饮品同样可以获得,无需专门饮用来自中国的茶叶,所以韦斯利努力劝诫人们,呼吁众人停止饮茶。而且在讲述完上述病症后,约翰·韦斯利还更进一步,又详细论证了饮茶导致的负面的经济社会影响,认为饮茶不仅危害健康,而且花费不菲,堪称一种浪费,戒茶后可以省下财物,用于帮助穷人。

表面看来,韦斯利基于饮茶危害健康这一缘由而反对饮茶,而且从其个人行为来看,他自身曾经一度戒茶,不过他并未长期坚持,而是后来又恢复了饮茶习惯,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老体衰,在星期天早晨韦斯利时常与牧师们一同饮茶,然后主持宗教礼拜活动。由现有材料观之,韦斯利似乎并没有因为再次饮茶而发作手颤症,他曾经痛陈饮茶有害于健康的说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韦斯利之所以反对饮茶,或许他在后面所论述的社会经济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国十八世纪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期,经济日益发展进步,工业革命快速启动,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约翰·韦斯利关心社会问题,痛心于国教日益腐败、道德衰落不振的社会现实,强烈的使命感唤起了其强烈的宗教热情,他和弟弟查理·韦斯利等青年才俊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国社会,著名的韦斯利宗宗教复兴运动由此兴起。约翰·韦斯利为非常严肃的社会道德家,他提倡严格的清教道德,主张勤勉工作与节俭的生活,因为茶在该时期其进口量较为有限,所以价格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价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韦斯利这位严肃的宗教家看来,饮茶属于可耻可恶的奢侈浪费行为,饮茶有悖于严肃、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积极宣传自己的反茶主张。韦斯利后来之所以恢复饮茶,亦与茶叶价格有关,因为随着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茶叶价格在十八世纪不断下降,它逐渐由奢侈品日益转变为日用消费品,融入了英国的社会生活,韦斯利也就无须固执己见,可以心安理得地与众人一起饮茶了。韦斯利掀起的反茶运动成为一朵小波澜,并未真正影响到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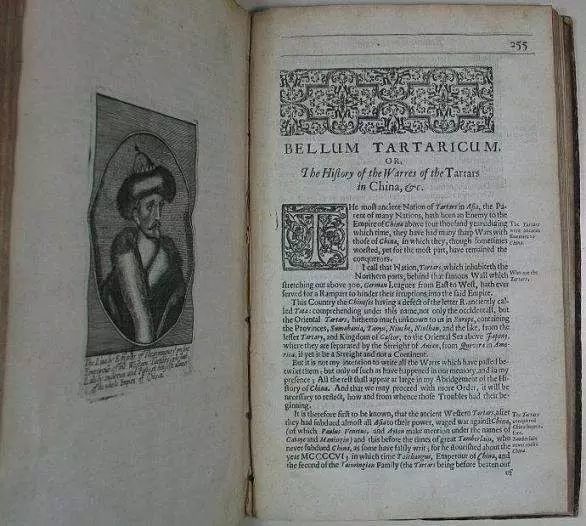
结语
新航路开辟开启了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传教士基于宗教热情而投入海外传教事业,成为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中国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福音与科学文化,同时将中国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经克陆兹、门多萨、利玛窦与曾德昭等人逐渐被呈现到欧洲人眼前,饮茶资讯在西方社会逐渐传播开来,为其成为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础。马礼逊、卢公明与郭士立等,由于拥有语言优势与知识文化的积累,得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茶叶贸易,侧身有利于扩大中西茶贸易的相关政治活动,为推动茶贸易发挥了独特作用。随着饮茶资讯的传播以及中西茶贸易的发展,饮茶在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流行起来,宫廷牧师奥文顿积极宣传饮茶的益处,宗教领袖韦斯利则因视其为奢侈品而反对饮茶,这些宗教人士影响到了饮茶在西方的传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担当了茶文化西传的中介,促进了中西茶贸易的发展,又对饮茶发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影响到了饮茶的传播与普及,可以说,基督宗教与茶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密切关联,值得学界予以关注。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年度项目《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刘章才,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韩国蔚山大学客座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茶文化世界传播史研究,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项目多项,在《光明日报》(理论版)、Asian Study(韩国)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

